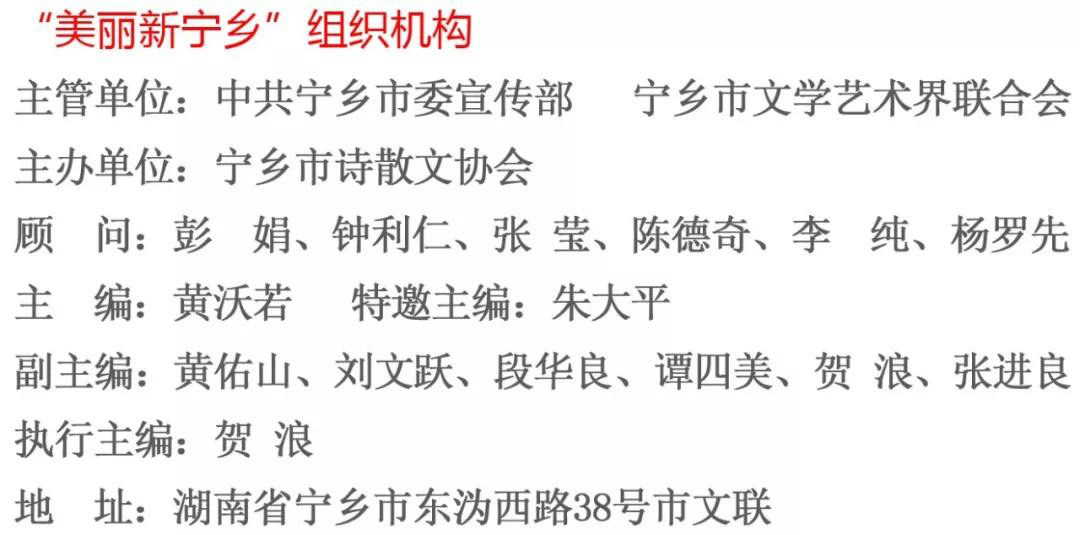来源:湖湘名人在线 时间:2019-02-27 03:18:43

花生那些事儿
作者:黄建军
花生,也叫落花生,又名长生果,我一直对它情有独钟,不管是生的、炒的、煮的还是油炸的,我都喜欢。一壶小酒,一碟花生米,也能满口生香,韵味无穷。
儿时,后山喻家坡那满坡蓊蓊郁郁,夹杂着黄色小花的花生,对我们这群满肚馋虫的小屁孩有着无限的诱惑力。即算是未成熟的“水泡子”,于我们也是无上的美味。放学路上,三五伙伴“密谋”着偷几蔸来尝尝鲜。惹得看守的余嗲嗲拖着扫帚撵得我们满山跑。

收花生的时节,更是我们的节日。满坡的男女,满坡的欢笑。男人们挖花生,女人们摘花生,小孩子们更是上蹿下跳,躺在花生堆里,可以放肆吃,放肆疯。
下午,热闹的山坡归于沉寂,只剩下余嗲嗲落寞的身影。母亲带我们兄弟几个到收获完花生的地里捡拾漏掉的花生。有时运气好,刨开土来,在一个土窝子里能找到五六粒圆滚滚胖嘟嘟的花生。我和弟弟一阵欢呼。小半天,我们的小书包鼓鼓囊囊,全是花生。母亲把花生洗干净加上一些桔子品、桂皮等香料,再撒上几把盐,便开始了每年必做的煮花生。不一会,清香四溢,诱人的香味弥漫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。一口香甜软糯的煮花生是母亲的味道,融入了我的梦乡,美醉了我的童年。

那年深秋,秋风紧,秋叶黄。趁月假的机会,回家看望父亲。刚回家门,父亲从烟熏火燎的灶房奔了出来,脸上黑一块青一块,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。他说母亲不在家,他正在给我们炒花生。父亲不善庖厨,好不容易炒好了花生,却是有的半生不熟,有的烧得乌黑。父亲面带愧色,说这么大的人了连个花生都炒不好。临了,父亲硬是要我们把他炒的花生带回了学校。
没成想,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到父亲的炒花生。没几天工夫,因天气转凉,父亲依然赤脚去挖收了花生的自留地,突然中风,倒在了地上,这一倒,竟是永诀。父亲一生劳作,生活极简。虽然干了三十多年的村会计,却从不张扬。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乡民、儿孙、土地,咀嚼着这带着苦味、涩味、香味的花生,泪落千行。

去年十一月份,到龙田家访,遇见了龙田老爹。老爹身材不高,衣衫破旧,年届七十,却依然硬朗,精气神很足。一进门,恨不得把家里珍藏的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。尤其那一大盆花生,粒子很小,斑斑点点,有一些还有虫咬的痕迹。老爹说,可别看这些花生没看相,但都是我自己种自己炒的,天然没有污染,可比你们城里的花生要好吃多了。尝了几粒,果然格外醇香。
小花淡色枚枚笑,瘦土肥荚串串争。花生有着乐观的品性,它是不轻易屈从于命运安排的。和花生一样,老爹艰难地拉扯大了年幼丧父的孙子。谈及儿子的早逝,老爹神情已没有悲伤。大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早已隐没在他脸上深深的皱褶里吧。说到孙子,老爹两眼放光,他说计划明年再多开垦几块土,多种些花生,再多干点零活,即算是砸锅卖铁,自己身上不添一根纱,也要把孙子培养出来。

分别,老爹要张网捕鱼,要下田捉鸭子,扛出花生,要送给我这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老爹的热情招架不住,只有落荒而逃。
归途,连绵的山峰在艳日的波光中闪耀着一片温暖,路边的清溪潺潺流淌着一份安详。都说上宁乡人特淳朴特厚道,大概是这青山,这绿水的熏陶和渐染吧。
小时候读许地山先生的《落花生》,这样说到:花生好处很多,有一样最可贵,它的果实埋在地里,不像桃子、石榴、苹果那样,把鲜红的、嫩绿的果实高高挂在枝头上,使人一见就有了爱慕之心。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,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,必须挖出了才知道。

这话深中我意。勤勉辛劳的母亲们,朴实无私的父亲们,坚强隐忍的龙田老爹们,他们把头低到尘埃里,捧出的却是一颗颗红彤彤的炽热的心。这不正是花生的真实写照吗?
闲园半亩弄春风,入土成蚕作茧中。
善把玉仁封壳内,深藏不露最心红。

作者简介
黄建军,男,宁乡实验中学语文教师,中学高级,长沙市骨干教师,宁乡市诗散文协会会员。从教25年,一直耕耘在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阵地。